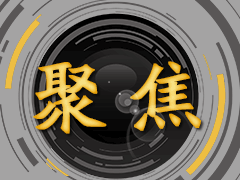旷远大漠
■王贤根
多少年过去,工程兵将士谈起那段艰难而又光荣的经历,总有一种悲壮厚重之感、扬眉吐气之情,又有一种让其留给历史的迫切使命感。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与不少曾经参加过那场“两弹一星”基地建设的老同志和他们的子女再次相聚。期间,他们以笃实的口气述说当年的一些场景。他们深刻的记忆、充沛的情感,甚至强烈的争辩口吻,令我深深感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创造者。面对他们青筋暴起、褐斑点点的苍老形象,我总想搜索他们青春芳华、朝气蓬勃时的风姿神采,这让我一遍遍地串联起那次深入戈壁大漠远行的回忆。
一
我们一行人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酒泉。城中的钟鼓楼上,四面镌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可见这座重镇地理位置的重要。
酒泉公园里,泉水依旧清清,泉池的水草悠悠飘动。我是从水草悠悠飘动所扬起的气息闻到酒香的。园内有棵枝叶繁茂、苍劲耸立的柳树,主杆两人也合抱不过来,人们说这是河西第一柳——左公柳。据史料记载,1871年,清朝将领左宗棠率军西征时,曾令将士沿途栽植柳树。园中这棵巨柳,相传是左宗棠驻防酒泉时亲手所栽。宁可信其真吧,它是一段历史的象征。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豪情与险难总是相生相伴。苦难创造卓越,苦难铸造不朽。
那一年,西北没有春天,风沙弥漫,铺天盖地。那一年,西北尽是春天,到处是一派蓬勃的火热景象。
新来的步兵师,任务是在离清水不远处的祁连山麓采石备料。某位打前站的师首长带领一行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原来旗政府的办公处,手里拿着粉笔准备为师机关和部队号房子,可机关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来到一片荒茫的戈壁滩上说,你们师部的驻地就在这块地方……
一望无际,唯独方圆一两平方公里的地方长有稀疏的树木,弱水河像乳汁般地浇灌这块土地,又缓缓地流向远方。他从地图上查到,这条细缓的河水是奔向北漠居延海的。当时,大部分干部混住土坯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铺盖卷起,床板即是办公桌。有一天,政治部召开部务会,研究冬季施工中的政治工作,突然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整个会议室顿时漆黑一团,只好点蜡烛,有经验的人急忙戴口罩,穿雨衣。待狂风过后,大家都变成“土人”。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刮石头满地跑。”战士的顺口溜是戈壁荒漠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施工部队的帐篷,安扎在半地下,这是吸取了刚进场时帐篷飞扬、人员失散受伤的教训。
备料部队首先为铁道兵师备足路基石,然后是为全面展开的基地内公路、机场、电厂、厂房、营房的构筑准备各种规格的混凝土石料、沙子和大块条石。先爆破,后碎石,筛选分类,场上石粉飞扬,收工时满脸尘埃。严寒的冬日,战士们双手冻裂,鲜血渗透手套。原先部队换装淘汰的旧棉衣作工作服,个把月就磨损得破败不堪,战士们开玩笑,近看像“乞丐”,远看像“绵羊”。可就是这样的队伍,上下班嘹亮的歌声、雄壮的吼声,此起彼伏,威震山谷。
二
西出阳关,古代丝绸之路进入西域段的第一个区间就是罗布泊地区,由此分南道、北道,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北缘西延。如今楼兰古国的广袤地域,已被浩瀚的黄沙覆盖,古国傍依的浩渺罗布泊,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收缩腰身。干燥,风沙,恶劣的环境,无常的气候,难以提供动植物的生存条件。
首批工程部队进入罗布泊腹地,生活和施工用水,都要用水车从150公里外拉运。施工区域关于水的故事、风的故事、节日的故事,一摞摞的叙述不完。有支部队凭借难得的秋高气爽之日,拟定皓月当空的夜晚开个娱乐晚会,文娱骨干们也想显身手,吹笛子、拉胡琴、唱豫剧、讲战斗故事,活跃部队生活。收工回帐篷,情况有变,每天送水的车辆连个影子也没出现,炊事班的战士急得跺脚,没水咋好下锅!电话联系,说水车途中抛锚。待到明月高悬,还没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晚会开不成,与其坐在帐篷里干等,不如到帐篷外坐着聊聊,一块唱唱歌。干渴咋唱啊?天南海北地说说,摆摆龙门阵吧!还是比谁都急的司务长说了话:每人发半根萝卜、三片白菜帮,解个渴充个饥吧。有这“高级水果”,指导员说晚会如期举行,哨声一响,全连集合,大伙儿边啃萝卜白菜,边欣赏欢快的小节目。时至晚上11点,水车还未到,大家只好宣布散会睡觉。第二天凌晨,水车喇叭声响,顿时唤起大家初醒的情绪。
当时,还有一支部队的施工地域在海拔3500米以上,空气稀薄,做饭夹生,饺子煮不熟,大家只好就烫烙饼吃。战士风趣地说:“这里不仅吃饭定量,而且空气也定量。”有年中秋节,部队用糖和面做成饼,用油烤黄,作为中秋佳节的月饼。为欢度中秋,各个连队吃完“月饼”穿上皮毛大衣,戴上皮帽,脚蹬大头鞋,集合到团部广场看电影。随着剧情的变化,战士们忽而欢笑,忽而叹息,正当入神之时,寒风袭来,很快乌云密布,大雪就纷纷扬扬地飘落。放映员用麦克风征求意见:“下雪了,还看吗?”“看!”场地上一片回声。风雪弥漫,指战员们的帽子、大衣上已经盖上了厚厚一层白。部队踏雪夜归,在各自的帐篷前嘭嘭蹦跳,抖落残雪,到了帐篷里又嘻嘻哈哈地谈论电影里的故事情节。
三
那次远行最后一站是马兰。离开马兰的头天傍晚,我们在基地的大院里漫步。宽敞的马路如同城市的街道,路旁的杨树间隔整齐,挺拔的身姿总让我想到它们就是基地将士的化身;丛丛簇拥的马兰花草,与其他花卉高低错落,交相辉映。在我们心中,马兰更显出它的坚韧与顽强。当年官兵将这块荒茫的塔里木盆地北部边沿,开辟为指挥中心和奋战在罗布泊腹地的数万将士的后方基地。一座称之为“马兰”的兵城,随着我国成功的核试验和将士的奉献精神而扬名四海。看着这绿树成林、鲜花遍地、整洁优美的环境,我们很难与昔日的荒芜和如今楼兰故地、大漠深处的苍凉连结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聊,都为几代基地将士的不懈奋斗所感慨。绿园东风航天城的情景也是这样。两座基地的导弹、核试验,虽已成为军史馆中的辉煌过往,但那时凝铸的精神依然是航天事业和新型军事装备测试的支柱所在。
大西北的整体环境,相对仍是艰苦的。在这里,滋润的六月天,对于我这江南人,感觉皮肤还是收得紧紧的。干燥,缺少雨水,是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地区的天然环境,但我们置于乐观开朗又有执着追求的马兰人中间,浑身好像充盈着勃勃向上的正气。这里的气场不断地调节着我们的心灵。
与送别的基地军人挥手告别。车子徐徐驶向缓缓上行的坡地。回首眺望,马兰基地一派葱绿,莹莹地闪烁在金色的朝阳里。
在回程的路上,车子突然嘎的一声刹住。我们下车,见有块龇牙咧嘴的山石拦在路中。司机说是刚刚滚落的。翻越天山的路,比过去好多了,但还有险情。我们合力将落石翻滚到一边,索性伫立路旁的高台,眺望群山。天山苍莽,雄健的山体时而兀立,时而舒缓,伸向远方。有只雄鹰从身后的山梁飞过来,在谷间平缓翱翔。谷底有片隐隐的绿,那里该有潺潺的水声吧。天山是新疆的母山,又是寥廓江天的子山。
直到司机说上车时,几人才依依难舍地走过去。我转过身,向来路深深地鞠了一躬……